岳永逸:个人的非遗的实然与应然
岳永逸教授对《文化转场:非遗散论》新书导言部分做了延伸,集中体现了作者近年来对非物质遗产保护运动的持续关注和深度思考。岳永逸教授首先肯定了我国目前非遗保护运动所取得的两点成就:其一方面唤起了不同人群的文化自觉乃至文化自豪,另一方面融贯了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情结,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今的非遗保护运动既是文化抢救,也是文化整合,和我国文化传统、行政传统中的移风易俗有着很多共同之处。然而,在民族国家的形塑之后,非遗又将何以使得民众与文化传承人身体力行地投入传承工作中呢?岳永逸教授围绕以下八个关键词呈现了自己的反思:匮乏、解释、公活、教育、人“生”、传统、政治、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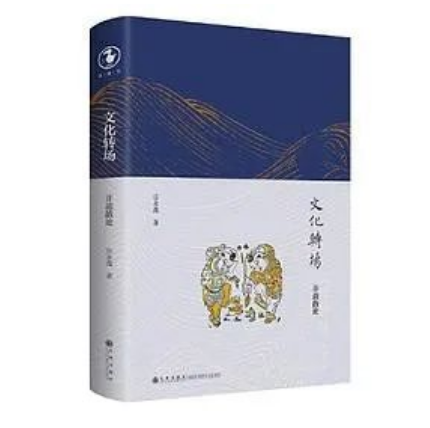
一、非遗的概念与解释框架
岳永逸教授指出,在目前关于非遗的讨论中,非遗的审美性、功效性等往往与非遗传承日常生活相剥离。香港大学郑长天关于瑶族“坐歌堂”的研究揭示,许多非遗并非产生于审美需要,而是出于生计策略、技艺,更多的是生产资料的匮乏。所以,从文化事项衍生的本身而非非遗的定义而言,非遗实际是由生活的技术逐渐增添了审美艺术的要素。由此来看,非遗其实是生活的技术或艺术,也是人与人交际的方式与表达。在仪式场合中,男女老少交往的方式也是社会之所以成为社会的外现形式。在前工业时期人与物的关系就是人与人的关系,这就意味着社会关系必然与大量商品生产的现代文明不同,现代社会中人和物的关系缺乏情感的联结,而非遗反映的正是物我互化的心性与习惯。在哈夫斯泰因所著的《制造非遗》一书中,非遗的定义颇具比喻性和诗意,在这样的非遗概念下,有必要设立一个新的解释框架。
此前,岳永逸教授在关于非遗研究的几篇文章中已提出了“房舍的馆舍化”与“馆舍的房舍化”这两个概念,意在强调房舍和馆舍这两种空间中呈现的非遗彼此互动、走近的状态。他指出,利奥塔提出“房舍”概念,以平铺的建筑形式代称与都市文明相对的前工业时期文明,但他忽略了二者之间并非简单对立关系,而是互相投影、呈现的涵盖关系。岳永逸以“馆舍”来体现“大都市”的隐喻与转喻,并指出馆舍(化)非遗并非对先在的房舍(态)非遗的置换,而是退化与蜕化兼具的覆盖及更新。结合马克·奥热“地点-非地点”的区分,他通过比较地点/房舍与非地点/馆舍两组概念,阐释了非遗的两种性质,认为非遗可能是具有归属感、关系性和历史性的,在身体力行之中,行者自然产生了恋地情结,故乡成为圣地和具有异质性的地方;而当非遗居于馆舍之中,它降格为空间而非地方,关系性、历史性也随之剥落。两个端点彼此走近与互动,非遗出现了馆舍的房舍化和房舍的馆舍化两类情况,如果说馆舍的房舍化,象征了都市人因疲惫不堪而生的逃逸形态、心态,那么房舍的馆舍化在呈现都市文明规训乡野的强劲的同时,也展现了乡民提升自己的诉求。房舍的馆舍化通常表现为非遗的表演,馆舍非遗必须服从镜头美学,从而逐渐丧失文化旨趣,走上肤浅的美学化历程,只追求外在的形式美,脱离了个体生命体验。他还指出,顾炎武《日知录》中的馆舍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天地山川相融、恢弘又兼具江湖感的馆舍样貌,如今按照镜头规则设置的非遗馆将人与展物相隔离,自然也就不会产生生命情感。
二、非遗保护运动下的两个案例
岳永逸教授进一步分析道,非遗保护运动使相对的“私有”让渡于相对的“公有”,与“小我”密切联系的社区传承、群内传承、师徒传承、家族传承向着散点、多元、不拘一格的社会传承转型。这就易导致对作为(开放性)共有资源的非遗的争抢,引发“公地悲剧”。非遗原有的丰厚地方意义在公有化过程中被湮没,并让位于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这就使得现今的非遗其实是复数的非遗。我们需要思考,在民族国家意识形态融入到评审过程中后,怎样才能让非遗和传承者生命历程产生关联,而不仅仅是供在馆舍中展演。他认为,对于非遗的有效保护与传承,应该是回归生活日常,回归传承主体一文化享有者那里,将其还原为可以支撑人之“生”、与个体生命、感受、体悟紧密相关的“非遗”。
他以两类生动的案例进行了解析。其中,关于汉沽飞镲和定县秧歌的传承体现了复数的非遗。汉沽飞镲起初主要用于渔业,但在描绘中也有飞镲表演。改革开放以后,用于生产或祭拜的飞镲快速融入到汉沽一带人们的白事中,和子孙是否孝顺相勾连,纳入了人们对于生者与死者关系的理解。由于飞镲与人的生命历程相关联,1990年开始飞镲就进入中小学,家长也比较支持孩子学习飞镲。所以在2003年非遗保护运动开始之前,本地已经有了申报非遗项目的社会基础和民意基础。在汉沽飞镲成功列入国际级非遗名录后,传承主体中围绕飞镲产生了一组地方语汇:“公活”与“出作”。“公活”专指以非遗名义进行的展演活动,这种展演因非遗保护运动而起,或者说是非遗保护活动使汉沽飞镲出现了一个新的类别,即非遗类别,因而传承主体的生活世界中,汉沽飞镲包括“出作”和“公活”两个部分、两种类型,大于非遗“公活”的能指和所指。这提示我们,在研究中一定要注意不能被非遗标准限制住,而是要关注它在当地本身是什么状态。在推动非遗保护过程中,非遗进校园是一种广泛采用的路径,但它局限于镜头美学的规训,可能缺少了原来能激发情感的内容,学生学习汉沽飞镲的热情远逊于20世纪90年代的状况。定县秧歌也与之类似,定县秧歌先从田间地头融入红白喜事,后来又在庙会上演出,前者被称为“挡小事”,后者被叫做“唱台口”,这两种形式的定县秧歌维持了30多年,为其后来被列入非遗名录奠定基础。然而,定县秧歌在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之后,不但未因政策扶持而日渐红火,反而不断萎缩。因此,岳永逸教授认为,我们在研究过程中,要充分尊重传承主体,深入体会其关联日常生活的神经末梢,自然就会发现“出作”“挡小事”“唱台口”等在非遗诗学中难以描述到的地气、生气与人气。尽管非遗化确实可以为具有调适能力的某种文化事象提供了衍生新类型的可能性,但将这一文化事象与大众生活形成牢固连接,不是非遗化的“公活”而是“出作”“挡小事”“唱台口”等文化形态。只有让非遗回归日常生活,关联个体生命价值,非遗语境下的非遗研究才有可能实现突围。 另一类关于学校传承的案例展现了非遗传承是另一种教育。1950年起全国各地开设的民族院校就是民族文化、地方文化进校园的实践,通过学校的方式对不同民族的语言文学、艺术文化加以集中保护,学者黄龙光关于峨山彝族花鼓舞的研究正揭示了这一点。花鼓舞在1950年代就步入了云南民族学院,1980年代峨山县民族中学鼓励学生穿着少数民族服装,学跳大娱乐等民间舞蹈。1989年,玉溪地区的民族中学引入了彝族达体舞改革课间操,每周一、三、五跳达体舞,二、四做广播体操。这种学校传承方式的有效性自然值得思考,因为这些以身体传承的技艺在学校里不一定能教授。但如今我国整个社会面临着重脑力轻体力的观念,而身体技艺的传承需要日常熏染和潜移默化,经验、直觉在身体力行修炼的过程中相当重要。通过言传身教习得身体性技艺的过程是人在其中历练与成长的生活本身,而不仅仅是外在于人,被对象化的知识。
三、生命历程与生活文化
岳永逸教授的人“生”概念具有生命历程和生活文化两个层面。生活文化就是一直处于变动之中,民俗的为“我”所用是民俗传衍的常态;民俗二次生命的获得,常常是从档案等书面材料中再出发的;多种因素交互作用下的民俗自身,同样具有适应性。多被讨论的礼俗互动概念也说明,传统中国的民间文化的演进,总是与精英文化交相互动而回环流转。乡风民俗的形成,更是经历了历朝历代统治者持之以恒的制度性的传衍教化,被民众内化为自觉进而反哺精英意识乡态的结果。
他指出,日本学者菅丰教授认为对于尊重民众多样化的文化实践并以之为研究对象的民俗学而言,“突出的普遍价值”几乎没有任何意义。人类的生活实践虽然不会被认定为世界级、国家级文化遗产,却是某个家庭的文化遗产,对个人自己是无可替代的重要存在。在注重高级别文化遗产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思考怎样反向落地使之回归家庭和个人,让我们心甘情愿地传习。再民俗化,不是对于民俗的片面使用,而是“把民变成民俗学者的现代性反思能力”,是个体对自己及其文化(遗产)之间关系进行反思和配置的实践,进而服务于个体生命感受、社群和谐、社会文明、国家康健和人类命运共同体铸造。从长时段来看,已经发生的非遗化仅仅是民俗传衍的一个方面或阶段。而个人的非遗一一非遗的个人(体)化,才是所有非遗的核心,才是将民俗非遗化后应有的终极旨归。
四、总结与讨论
岳永逸教授的讲座给非遗工作者和师生们均带来很大启发。两位非遗保护者都结合自身在非遗进校园过程中所遇到的困惑和疑虑,表示对岳永逸教授关于非遗传承的思考深感认同。西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满珂教授也展开对话,提出源于民众的非遗是否要回到民间吸引年轻人的问题。岳永逸教授认为文化的传承和演进有其自身规律,文化建设不是目的,应当顺势而为、尊重民众的选择。还有学者就非遗中各主体之间的关系提问。岳永逸教授指出,非遗对于老百姓来说是一个用来应对统治的策略话语,我们需要注意到其中的动态过程。
最后,萧放教授对此次讲座进行总结。他指出,本场讲座适逢《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发布20周年,特别有现实性和针对性。非遗保护是国家政府的重大工程,非遗文化传承工作应当注意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讲座中分析了两类关系:一是国家的非遗和生命个体的非遗之间的关系。我们应当思考在国家文化建设的宏大叙事之后如何看待生命个体的处境,这也是所有文化建设的根本目标。在非遗保护的宏大趋势之下,个人性的情感和生存需要应当得到重视。另一个关系是传承的非遗和公共表演的非遗之间的差异。作为公共表演的非遗脱离了产生的具体语境,其形式、功能和作用也随之改变,而非遗想要传承下去就必然要服务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为人们的生命历程和幸福感服务,因而非遗的传承就不能仅限于展演,我们需要辨明传承与传播的关系。虽然菅丰教授认为民俗学研究多样化的文化实践所以不必关注突出的普遍价值,但非遗工作的价值正是在回归生命个体的追求中展现出了超越具体案例的普遍性。

